close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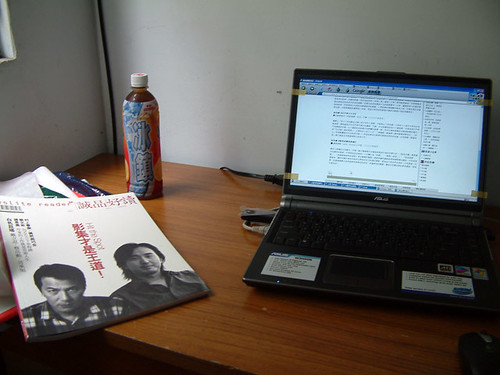
這是我的第一台筆電,這張照片是我在淡水宿舍寫的最後一篇網誌,然後那台筆電的硬碟掛點了,到現在還沒換新的。

當時我正在打包、將五年的東西裝箱、扔去、販賣、轉送,最後只希望來個人也把我打包帶走。
Dear K:
我擔心屆時我繳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,所以月初就開始寫了。沒想到一個晚上不到三個小時我便盡數完成了。
那些我買的雜誌到現在都還沒有拆封,倒是新的網路媒介(噗浪)再度吸引我眼球的注意,然後我覺得噁心了。不過這倒也不是什麼重點,而是我枕頭旁邊的那一疊書籍提醒了我一些事情,那是關於平衡。工作超過一年後才找到:愈是在工作上受氣,愈是需要閱讀來平衡心裡的那股紊亂的氣息(姑且爭之為鳥氣)。我才發現,床頭堆了《海神家族》、《物裡學》、《哀艷是童年》以及鐘文音的《慈悲情人》,都是在心血來潮從書櫃取下卻始終沒有翻閱的打算。,這四本書裡頭,除了《物裡學》李明璁是男性以外,其他三位都是女性,我並沒有特別不喜歡男作家(但我始終沒有辦法看完一本駱以軍的作品,反倒是牢騷嘮叨的唐諾我很喜歡),只是女作家更能夠吸引我的眼球,尤其是當我看完陳寧的《風格練習》,清新的令我開心。
我承認,我喜歡重口味的作品,感情繕寫的愈是濃郁,愈是正對胃口,不過老是讀那些陰暗裡邊的文字,那種清淡爽朗的日系風格,往往就是我逃逸的路線(或者是搞笑的伊坂幸太郎也可以)。所以我在噗浪上說:因為《附魔者》的情感過濃,我險險在閱讀的過程中,差點忘了呼吸,窒息在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漩渦中。她寫:一開始就錯了,到最後也不會是對的。或說,我正在文字的世界裡頭揣謀殺人的方式,想起觀看《口白人生》的趣味。愛瑪湯普遜所飾演的老煙槍作家,不斷的思考要怎樣殺死他的主角,而大學教授也向男主角提到這女作家一貫的風格:作品裡頭的主角最後都會翹辮子。《時時刻刻》當中,吳爾芙看見花園裡死掉的小鳥,作品當中她讓詩人死去,而20世紀裡的戴維洛夫人,目睹好友自殺墜樓身亡。
他們說,描寫死亡是要提醒生者珍視生命,另外一種的死亡是惡搞的恐怖。終於看完自租書店借來的《慢慢來,比較快》,是九把刀在三少四壯專欄的集結成冊。我不得不驚嘆九把刀天馬行空又令人驚喜的想像力,提及千萬不要在深夜抬頭看大樓的上方,那跳樓自殺的亡靈將會吸引你走到大樓的底下;它不斷的重複死亡的過程,當它從大樓一躍而下,它的靈魂將會撞入你的身軀,那重力加速度將會壓死你的靈魂,而它借屍還魂,於是這張臉孔底下的魂魂並不是同一人,而是錯置。這種聽起來毛骨悚然的自創鄉野怪談,儼然成了都市版。
《口白人生》裡,哈洛改變了自己的人生,漸漸的變得有人味,喜歡上一個人,最後卻死在公車的猛然一撞。這是部後設的作品,老煙槍作家站在桌上幻想自己在頂樓的邊緣,或者到醫院去找即將死掉的病患,或者是在大雨的橋墩附近試圖撞見一樁連環車禍。這些死法都無法在它的作品裡頭撐起重責大任,必須是具有深遠意味的一種死法。於是在滾落一地的蘋果想到了最最最偶像劇的安排---主角為了搶救或者是撿某個物品的時候,死在高速行駛來不及煞車的公車輪下。
我則是讓我的被害者在浴室裡頭掛點。
你知道我喜歡唐立琪的,2009星座書裡頭寫到我今年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其三之一,就是與家人的關係。「總歸來說,今年的成長關鍵掌握在:外界的變化、你自己的變化、和家人間互動的變化,三種變化加總而成,任何一種因素微調都會「牽一髮而動全身」帶來許多改變,務必留意不要再粗心戲謔或白目不在意去面對周遭的人、事、物,莫名投下變數而不自知。」上個禮拜,我星期六必須要上早班的星期五夜裡,老爸邀我喝一杯,我因為隔天要早起而選擇陪他坐在餐桌前說古,不願意黃湯下肚。聽他娓娓道來關於家族那條隱形的心結,在夜裡浮上餐桌,透過一杯酒而發酵。他提起已經去世的爺爺小時候的管教方式,讓他選擇離家出走不願在待在恆春,他到高雄找工作,輾轉在外流浪一年多,機緣巧合跟著水電師父當學徒。
28歲的他,曾經也擁有好幾名員工,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水電行,包下了好幾個工程,好幾地在進行。那時候,爺爺奶奶以及叔叔以及堂姊們搬來一起住,家裡的負擔變重,漸漸的感到吃不消。在某個他並不在場的爭吵過後,喪兒之痛的傷口狠狠地被扒開,上頭撒滿了婆婆口不擇言的毒語,場面是爺爺朝鐵桌狠狠摔去木椅,堅固的鐵桌凹了個大洞,在場的所有人心裡頭也破了個大洞,再也無法縫補痊癒。然後他們便陸陸續續搬離這個家,剩下我們四口。
那個他獨飲的魔幻時刻,揭露了小時候一直無法理解的家族軼事,為什麼他們都要搬離呢?
唐立琪寫:無可迴避的家族問題。「這些年來,有些射手座刻意不面對家人、和家人疏遠,或面對家人的態度都傾向詭異或顯露不耐。但今年最好面對現實,也許在家人心中你是麻煩人物所以也懶得多說,或在家人是你的麻煩能離多遠就多遠;與其說是要射手面對家人,不如問射手是否願意面對自己的內心,不安內如何攘外?」
我會提起這件事情是關於上回提到畢業,不得不提及回台中(或者是所謂的回家鄉)。我依然能夠憶起初搬回三樓自己的房間那段日子感到的不踏實,以及鎮日惶惶不安。我不太能夠適應我離開台北那座五光十色的城市(沒有了捷運,我得靠自己能騎多遠算多遠),離開居住五年充滿大學酸甜苦辣回憶的淡水小鎮,回到這個東南西北我之知道附近7-11怎麼走的出生地,我總覺得我無法完成那塊失落的拼圖,缺了很重要的一塊,這麼一缺就是五年。時間空間上的斷層缺口,心裡頭對於原生家庭的高築城牆,封死我跟家人溝通的每一條路。
我覺得我是有內涵的人,卻忘記,比起他們,他們是有故事的人。
在錯綜複雜無解的敘事裡頭,老爸不斷的提起:我也不知道當時你爺爺是怎麼想的......的那個當下,至少我知道老爸是怎麼想的。這一家四口裡頭,十幾歲逃家在外流浪渴望安定的老爸,小學畢業就到工廠當女工現在非常強悍的老媽,與我相隔六歲飽受呵護男朋友是自願役的老妹,以及出去就像丟掉、回來就像撿到的我,試圖在這張家庭衛星雲圖裡,找到屬於自己的軌道。
我突然想起《風格練習》裡我非常喜歡的一篇〈命運之門〉:『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喜歡探究命運的必然與偶然,一九八一年的「Blind Chance」(機預之歌),從追不追的到火車這點分叉出三條截然不同的命途。這些情節看著深刻,但我沒有給說服。......(中略)......這樣的因果圖像,不僅僅是某點與線,而是懷懷相扣連成網狀的大迴旋。
看來看去,我還是傾向認同希臘戲劇裡的命運觀,是命運選擇人,而不是人選擇命運。換言之,宿命論,必然遠大於偶然。命運之門的開與關,沒有遲沒有早,只有剛剛好。』
已經無法這麼推論:假若當年老爸不要逃家、假若老媽當年沒有北上去看住院的老爸、假若當年我沒有填淡江這個志願、假若當年我沒有加入社團、假若假若假若,不管在多假若,我們都無法像電影《回到十七歲》一樣回到當年,去幫助什麼。九把刀寫:『在年輕網友們的討論裡,大人被妖魔化成了一種發出腐敗氣息的生物,在此論述裡,中年不再是一種年齡的界限,而是行為舉止與青春之間發生了強硬斷裂,於是小鬼便成了大人------而且還是無法想起小鬼在衝蝦小的那種死大人!
或說中年也沒什麼可怕,因為我們不見的要用狼狽不堪的姿勢步入中年。
今年二十八歲的我,真誠的希望我到了所謂的中年後還是偶爾奢侈地夢遺,依舊相信我所說的「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,才有實踐的價值;即使跌倒了,姿勢也會非常豪邁。」
然後,每天醒來刷牙時,清楚知道鏡子裡的人是誰。--------一個不需要用名片上的字句,去解釋我如何存在的誰誰誰。』
他說的滿不錯的,不是嗎?一如青峰在演唱會說:溫柔的推翻這個世界,把世界變成自己的。不要變任何人期望的自己,而是自己期望的自己。一路以來的跌跌撞撞,不管怎樣,最終還算修成正果(我如此自以為),知道自己是誰,愛過誰,喜歡音樂、喜歡電影、喜歡閱讀、喜歡書寫、喜歡自己。
Know Thyself,希望你能夠在畢業、入伍前、退伍後、工作前的這一段魔幻時刻裡,找著你自己。並永遠記得。
共勉之。
延伸閱讀:
陳寧《風格練習》

九把刀《慢慢來,比較快》

全站熱搜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